第三届常德原创文艺奖获奖作品: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从陌生回到原点
——王跃文长篇小说《爱历元年》评析
文/张文刚
一
毫无疑问,王跃文的长篇小说《爱历元年》①是一本描写情爱的小说。书名“爱历元年”有着耐人寻味的寓意。在人生婚恋的悲喜剧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恋爱原点,亦即“爱历元年”,而且一般而论,这个原点或者“元年”都是美好的、值得纪念的。从这里出发,有的人不断发展、丰盈自己的爱情生活和心灵世界,与所爱的人携手到老;有的人渐行渐远,最终偏离爱情和婚姻的轨道一去不回头;有的人在尴尬的人生境遇和心灵迷惑中苦闷徘徊,离开原点最后又回到原点。《爱历元年》描写的正是后一种情形,主人公孙离和喜子,这一对曾有过甜蜜爱情的夫妻,在事业上苦苦奋斗,一个成为了专业作家,一个成为了大学教授,可谓风光之至,但是在爱情婚姻的旅途上却经历了从浪漫诗意的顶点跌落情感冰点,再到自我救赎、回归原点的曲折过程。就像他们的名字所暗含的那样:由近乎离散的无奈到回复原点的欣喜。这看似简单的回归,实则是一种超越,是经历恩怨风雨和心灵磨砺之后的自我净化和自我完善。
进入婚姻围城后,孙离和喜子似乎瞬间就变得“陌生”,成为了陌生的熟悉人和熟悉的陌生人。“他俩甜蜜了没多久,慢慢就开始吵架。大事也吵,小事也吵”,以致“有时候会忘记争的是什么,反正拧着对方就是赢家”。这种夫妻关系日趋紧张和陌生的结果,就是各自有了婚外恋情。于是两性之间的亲近与陌生被迅速置换。孙离与李樵因为“采访”相识而感情闪电升温,旋即走进两心相悦的暴风骤雨;喜子和谢湘安由于同事关系,在经历几次偶然事件之后,随即卷入两性狂欢的洪流。本应属于夫妻之间的种种亲昵和缠绵,由于夫妻之间的“陌生”而转移到了“他者”身上,“陌生人”似乎不需要太多的过渡和铺垫就成为了“宝贝”和“亲人”。夫妻之间的陌生不仅加深了相互的隔阂和婚姻关系的危机感,同时还衍生了副产品:父母和儿子之间不断加剧的陌生感;对自己身体和心理的陌生感。在父母没完没了的争斗中,儿子变得越来越冷漠和叛逆,也越来越陌生。在紧张的夫妻关系以及乐此不疲的婚外恋情中,孙离慢慢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陌生”,前列腺,失眠症,使他“越来越不能控制自己”;喜子常常滋生的一些奇怪的念头和想法,使她对自己的心理意识感到“陌生”,自己变得都不认识自己了。现代社会,人生仿佛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被陌生化、甚至被异化的过程。陌生化以及情感的转移,当然有着种种原因。首先来自于人的一种“现代性焦虑”,现代社会所宣示的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以及加在人身上的种种压力和束缚,在改变人的心境和命运的同时,也使人寻找合乎自己的途径释放内心的重荷,以求得暂时的心理满足和快慰。其次是一种社会风习和潮流的影响与裹挟,伴随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人们越来越追逐对财富和声色享乐的占有,也越来越丧失了维护幸福和恪守道德底线的能力。再次从更内在的方面来看,是人的固有心理和欲望的驱动,喜新厌旧的人性弱点和欲望的洪水猛兽,如果不加以节制和防范,则必然改变人的生活链条和心灵生态。
演绎人生的陌生感和荒诞感,当然也能表现出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爱历元年》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作家合乎逻辑地描写了人物的情感“回归”,并由此传达出一种温暖的气息。心灵生态的失衡,也唯有借助心灵的力量来调节和修复,才能达到新的平衡与和谐。当喜子沉醉于婚外恋情带来的喜悦和神秘的时候,内心的愧疚和忏悔也把她推向了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在经过内心深处十分痛苦的挣扎之后她慢慢回归到平静的家庭生活。相对于喜子的“主动撤退”所呈现出的决绝姿态,孙离体现出的是一种“被动回归”的无奈,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在孙离的婚外恋情中,合与分就像一场“醉酒”的宴会,醉不需要理由,醒也不需要理由。当李樵提出“分手”的时候,孙离陷入了被动的尴尬和极度的痛苦,而在李樵那里则是平静的、无所谓的。熟悉、亲近的人瞬间又变为陌生。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追问的通过婚恋体现出来的“现代性问题”。作家并没有给予小说中的人物更多的道德评判,只是让人物在自身生活逻辑的演绎中去认识自己、反思自己,从而调整自己;也唯有自身的反省和调整,才足以投射出灵魂深处的光芒。这一点在喜子的身上体现得更为充分和彻底。小说最后用“错”和“病”来结局,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客观描写,当然同时又是一种立场:有错就得“纠错”,有病就得“治病”。孙离和喜子的儿子出生时由于医院过错与别人家的孩子“错抱”,不仅仅是亲情关系的错位,也指认了孙离和喜子自结婚后感情的背离和错位,因而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要摆正位置,不是简单的交换或归位,还需要长期的心理疏导和矫正,这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小说借孙离的弟弟孙却身体上的“病”以及病痛之后的大彻大悟,实际上暗示人的膨胀的、失范的欲望也是一种“病”,一种更摧残人、折磨人的病。孙却的病除了就医外,乡村游历成为了他身体康复的一剂药方;同样孙离和喜子心理上的“病”除了从外界斩断病源外,还需要“心灵乡土”的静养和滋补,那种来自记忆乡土的淳朴良善和心灵与人格深处的洁身自好和道德操守是防治和解除心理疾患的“美丽山水”。孙离和孙却两兄弟的名字也预示着他们到头来离却、了却情场、商场乃至于官场的种种是非和羁绊,回归本来拥有的安宁幸福的生活。王跃文在近年的一次访谈中曾说自己出生于乡村,对乡土怀有深厚的感情,“正脉脉含情地回望着乡村”②。这也许意味着作家今后的创作就题材和价值取向而言会有所转向,《爱历元年》应该说就是这种转向的开端,美丽乡村,包括内心深处的乡土记忆和自然神性都在召唤着作家“还乡”。
二
《爱历元年》借男女之间的情爱之旅,表现了丰富的人性内涵。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精妙的比喻,当别人怀疑孙离的推理小说的意义时,“他感觉这个世界就像放多了沐浴露的浴缸,人坐在里面看到的只是厚厚的泡沫。他的写作就是要撇掉浴缸上面的泡沫,直抵水底真相。”引申来看,《爱历元年》就是要撇掉情爱的以及种种人生世相的“泡沫”,直抵人的本来面目和人性的真相。王跃文被称作“官场小说第一人”,他本人并不认同,因为他认为自己“写的不是官场现象,而是官场人生,是社会生态系统”③。“官场”只是一个题材的入口,人生百态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才是文学表现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历元年》和王跃文的官场小说是相通的,都是通过人情世故表现“社会生态系统”,只是这里的“官场人生”,被置换成知识分子的情感历程。与权力欲望、物质欲望等一样,情感欲望也是以占有和享乐为目的。这种欲望,用小说中的一个物象来形容的话,就是“蚂蚁”:“一只蚂蚁正顺着樟树皮的裂纹,急匆匆地往上爬”,欲望的蚂蚁,总是在残缺的地方突围和攀升。跟其以往的小说一样,王跃文主要把笔力投向“人性的暗角”,揭示和批判人性的弱点。正如小说中主人公观赏芦苇景色时看到的一首打油诗所写的那样:“芦苇虽美景,小心藏歹徒”,人正是这样的“芦苇”,莽莽苍苍,芦花飞扬,而心灵深处也许藏着“歹徒”。《爱历元年》就表现了“歹徒”在人内心里的蛰伏、蠢蠢欲动以及对道德底线的跨越,无论是夫妻、情人之间,还是朋友、长幼之间,作为人其真实的一面如谎言、伪装、嫉恨、冷漠、臆测、小心眼、小手腕等种种心理意识和行为举止被毫不掩饰地勾画出来,成就了丰富、立体的人生画卷。
小说在表现“人性的暗角”的同时,也在努力发掘“人性的光芒”,并力图借此照亮人性的幽暗。喜子的觉悟和警醒,在情欲面前的毅然止步;孙离的被迫接受分手,在忍受痛苦之后对温暖现实的贴近和融入;孙亦赤流浪途中对亲人的牵挂和念想,对“回家”的诗意吟唱;孙却摆脱名利场,回归清净生活的畅想,等等,都是一种人性的突围,走出心灵“暗角”的一种努力和追求,都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当然,这种突围是极其艰难的,是一种自我斗争,一种心灵搏斗,要以牺牲个人的快乐和自由为代价。这种免于沉沦和毁灭的自我救赎,是自我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是穿越心灵暗区的一缕晨曦,导引人到达更加敞亮而美好的世界。王跃文曾谈到“敬畏”,他说,敬畏既有现代人的自我约束,也有现代人的自我救赎。这是一种道德力量的外化。有信仰、有原则的人才会有所敬畏。很多人把所有的信条都放弃了,没有任何原则和道德底线,只剩下欲望。欲望像一个至尊魔咒,人成了欲望的奴隶,成了权、钱、色的奴隶。有敬畏的人也是一个能自我认识、自我反省的人。人有欲望是事实,但人的美与生命的价值则往往是超越这种“唯实”后所表现出的自由与庄严,人需要对自我进行洗濯④。可以说《爱历元年》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欲望失范之后对生命和情感的“敬畏”,通过自我认识和自我洗濯后到达一种“自由与庄严”的生命境界。
如果按照当前某些流行小说的写法,完全可以写成一个夫妻离散的悲剧,或者婚姻重组的喜剧或闹剧,可是王跃文没有按照这个俗套来构思,而是在表面一池静水实则波翻浪涌的节奏和韵律中,写了一曲夫妻相互背离之后又和好如初的正剧。作者以一种平静、带着几分纯净和浪漫的情怀与眼光来看待和描写情爱生活,因而就没有那种低俗和庸俗的格调,即使是爱情幻想和性爱描写,也显得较为含蓄和内敛,甚至还有几分诗意。比如写孙离对异性的幻想,总是隐现着“兰花”的形象。在他所接触的异性中,刘桂秋、李樵、妙觉等女性都在“兰花”的映衬下,显得楚楚动人和值得念想。兰花以其雅洁的气质和幽香的气息照亮了他内心的混沌和期待,因而对女性的幻想和爱恋也几近升华为一种君子品格和典雅情怀。这种含蓄蕴藉和诗意化的想象与表达,还体现在一种文化氛围的营造和渲染上,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谈佛论道,有时候被恰到好处地穿插在文本中,成为对世俗生活的装饰、渗透和洗涤。这种诗性的、温暖的气息,还反映在作者通过情爱的触须延伸到社会世相,表达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和关爱。作者通过艺术形象表达出来的对某些社会问题的忧虑和批判,对社会底层卑微者的体恤和关怀,都体现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正因如此,当我们跟随主人公的步履踏上“回归”的路程,向着美好的“原初”贴近和超越时,我们的心中在升腾起一股暖流的同时对社会和人生也会寄予无限的希望。王跃文曾这样表白:“文学也许应该超逸出生活的真实,给人以理想和希望。”⑤这是作者所追求的一种愿景,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应追求的文学理想。
不仅如此,意义还体现在艺术的层面。从陌生回到原点,也可以理解为拒绝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表现,拒绝那些人工雕琢和刻意安排,回到最朴实、最本真和最自然的表达,应该说这也是艺术的“原点”。文学艺术的起源和生活密切相关,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近现代以来,一些作品以反理性、反秩序为旗号,通过变形、拼装、夸张、跳跃等“现代”“后现代”的艺术表现手法,来揭示现实生活和人性,虽然也给人以新颖的审美感受,但似乎和普通人的生活隔得较远。王跃文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平淡、自然的笔法将几乎原生态的生活和盘托出,让欣赏者没有任何阻隔地融入其间,在感同身受中理解生活、感悟生活,进而创造生活。在他这里,也有“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东西,但主要不是作为一种手法和技巧,而是一种犀利的眼光和内涵的沉淀,是对生活本质的把握。王跃文的这种回归艺术原点的风格,不仅是一种艺术修养,更是一种创作观念和价值追求。
三
正是借助日常生活的描写,表现人的感情纠葛和心灵历程,因而在艺术构思和表达方面体现出鲜明的个性追求和特色。往大一点的方面讲,王跃文笔下的生活气息和情致有点“红楼遗韵”;往近一点说,王跃文的艺术表现和风格可以看到鲁迅的幽默、机智、悲情和讽刺,老舍的逼真而细腻的描写,钱钟书的精妙的比喻,当然还有融合现实主义精神和理想、浪漫情怀的艺术追求,从中可以感受到巴金、沈从文、汪曾祺等大师的流风余韵。
从陌生回到原点,是生命和情感的跌宕与回归,原本可以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大做文章,可是作者偏偏没有刻意经营故事情节。夸张一点讲,这是一本没有故事只有真实、没有情节只有情感的小说。或者说,它没有完整、清晰的外在的情节链条,只有生活的“场域”和气息,只有内在的情绪流和情感流。情感的发生、发展、高潮以及突转或渐变,及至沉潜、回归而趋于平静与和美,这就是小说内在的情节。那些猎奇求异的读者可能会失去阅读的兴趣与耐心,只有那种善于体验、感受、咀嚼生活和人生况味的人方能受到浸染和感动,并领略小说内在的韵味和魅力。如果借用小说中一个常用而具有动感的句式“越来越”造句的话,就主人公孙离和喜子的生活与关系而言,在小说的前部分是“越来越”走向紧张和陌生,在小说的后部分是“越来越”达成谅解与和谐。这就构成小说的一种情绪节奏和情感线索,从这方面来说,小说的结构是完整的,也是完美的。这样一条隐形的“情感线索”串连起来的是日常生活的场景和琐事,有时在这条线索的诸多节点上是一种相似、相同的生活场景和情景的“复现”和照应。喝茶吃饭、赋诗作画、散步休闲等生活内容以及赌气争吵、思念玄想等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被作者不厌其烦的描写,成为涵容情感而又过滤、沉淀情感,还原人性的“容器”。推动内在情感发展的动力是人的欲望和对欲望的节制,这是一种“内生力”,是一种比外在的逻辑推理导致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更为强大和持久的力量。可以说,《爱历元年》采用的是还原人的心理意识和欲望的叙事策略。
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王跃文的小说,有着丰盈的日常生活细节描摹与纤毫毕现的心理刻画,细微到人物的一个眼神,一个称谓,一颦一笑,连语调与姿势等不经意之处,他都不含糊交代,而是着力描绘。”⑥《爱历元年》作为一部情感小说、生活小说,当然就更注重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文本中有大量的心理感觉和心理现实的描写,这种描写把心理和“此在”与“彼在”联系在一起,即描写人物生活现实的改变带给人的强烈的心理印象和感受,以及人物过去的生活情景在心理上的重现和强化,进而通过心理媒介传达出更为深广丰厚的内容。人世间最能使人产生心理变化的,从现实功力的角度讲也许除了金钱和权力外,就是男女之间的“爱”,这种爱能让人上天堂,也能叫人入地狱,还能令人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进退两难、苦苦挣扎。《爱历元年》通过男女情爱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正是这样一种情形。孙离与喜子初恋时节的怦然心动以及婚姻关系阴晴分合带来的心理反差,孙离与李樵、喜子与谢湘安婚外恋情存续阶段的欲生欲死,喜子努力挣脱不伦恋情的心理搏斗,孙离与情人被迫分手后的失魂落魄,等等,都刻画得极为细腻和逼真。同时在这种心理刻画中,常常把现实和记忆、想象和真实、快乐和痛苦等情景和情绪打通,形成一种错位或强烈反差,让人物的心理活动更加微妙深隐、跌宕起伏。与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一样,这部作品也表现出对生活细节及其人物行为依据与心理逻辑的特别关注⑦。作为情感小说、生活小说,《爱历元年》的细节在承载着一些象征和寓意之外,从整体上看具有十分浓郁的生活色彩和气息。结婚生子、衣食住行、锅碗瓢盆,“一地鸡毛”似的生活,在教人脾气变得“越来越坏”的同时,也赋予小说细节平淡甚至琐细的意味,有时候还免不了近于拖沓和冗繁。同样诸多描写两性之间幽会、亲昵、思念、期待的细节,在服从人物的个性和心理刻画的同时,有时也给人一种甜腻的感觉。
从陌生回到原点,体现在艺术思维与表达上也有许多创新之处。夫妻关系的紧张导致陌生化,以及婚外恋的发生、发展带来的欣喜和狂热,这些东西在人们的识见和经验世界里是太熟悉不过的事情,对于“熟悉”的内容,作者偏偏进行“陌生化”的处理,即饶有兴味、不胜其烦地进行逼真、细腻的描写,如散步、吵架、喝茶、吃饭,及至亲吻等等,都被作者拉长、放大或放慢节奏来写。功夫也许就在这里,把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进行艺术地审视和表现,从个人的生活琐事触及社会现实,表现人的“当下”处境和心境,从生活的表象进入心灵的深度和人性的富矿,这些都需要相当的铺展能力和聚焦才能。王跃文曾说:“我平时观察生活,也是力图冲破重重话语魔障,力图直抵真相和本质。”⑧可见这种艺术表现能力,其实来源于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深刻感知。同时,在作者的艺术思维及表达中,还常常有“突转”及复杂化的描写,即从陌生切换到熟悉,或者从熟悉切换到陌生,以及描写熟悉中的陌生和陌生中的熟悉。迅速转换或感觉的复杂化、多样性描写,在造就艺术的新奇效果的同时,表现了生命的自由与局限以及种种复杂难言的生命体验,对生命和社会有着更多本质的探询。作为一部情感小说和生活小说,由“放”而“收”的内在情感线索,也带来结构上的铺垫、悬念设置与前后勾连和照应。亲子关系的“错位”、孙离的“桃色风波”、江驼子的身世和结局等等,在前面看似不经意的描写中,实际上草蛇灰线、环环相扣,到最后抖开包袱、曲终落幕。这些虽算不上艺术上的出巧和创新,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特别是作为一部情感小说和生活小说,也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在呼应、助推内在情感线索发展的同时,完成了人物命运的塑造和艺术结构上的照应。
(原载《芙蓉》2015年第1期)
注释:
①王跃文:《爱历元年》,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②夏义生,龙永干:《用作品激发人性的光辉——王跃文访谈录》,《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2期。
③吴义勤,方奕:《官场的“政治”——评王跃文长篇小说〈大清相国〉》,《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6期。
④夏义生,龙永干:《用作品激发人性的光辉——王跃文访谈录》,《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2期。
⑤刘起林:《官场小说的价值指向与王跃文的意义》,《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
⑥刘起林:《官本位生态的世俗化长卷——论〈国画〉的价值包容度》,《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5期。
⑦刘起林:《官场小说的价值指向与王跃文的意义》,《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
⑧夏义生,龙永干:《用作品激发人性的光辉——王跃文访谈录》,《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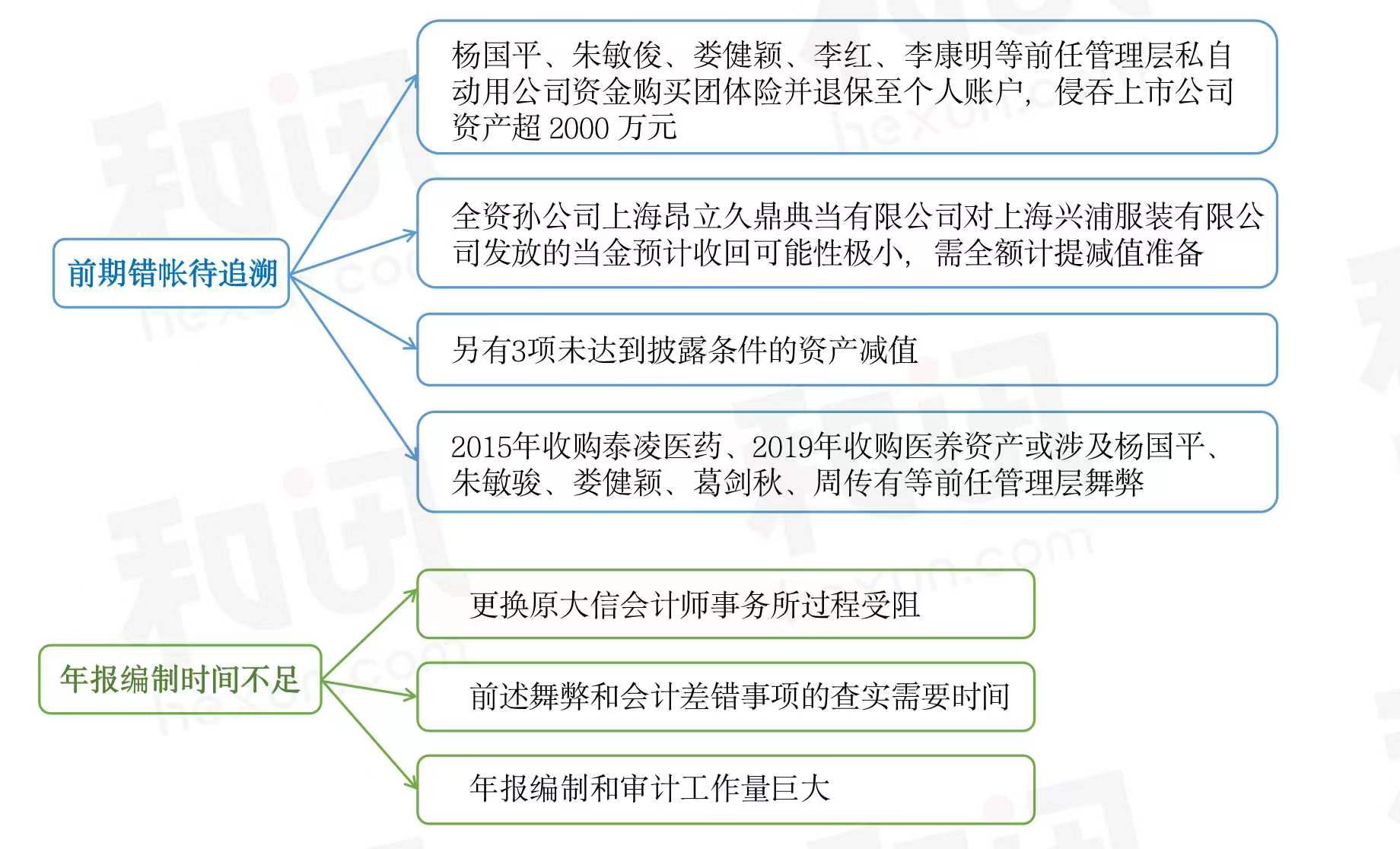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